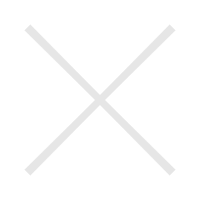摄影有时给人会造成一种错觉,它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诞 生的,由于它的机械性,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利用机器的成像原理将我们已知和可见的事物通过平面再现而已,我认为,机械所带来的快捷性不应当成为创作意识的束缚,相机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力来实现创作思维,就像手握一支画笔一样。《道可道》是我用12◦胶片拍摄的作品,在我的眼里,我将所见到的带有符号性的景观予以柔焦与虚化,镜头中的对象因此变得抽象,说不清道不明,只剩下形与色,将人类最本质的权力欲望隐藏在画面的背后。

摄影有时给人会造成一种错觉,它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诞 生的,由于它的机械性,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利用机器的成像原理将我们已知和可见的事物通过平面再现而已,我认为,机械所带来的快捷性不应当成为创作意识的束缚,相机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力来实现创作思维,就像手握一支画笔一样。《道可道》是我用12◦胶片拍摄的作品,在我的眼里,我将所见到的带有符号性的景观予以柔焦与虚化,镜头中的对象因此变得抽象,说不清道不明,只剩下形与色,将人类最本质的权力欲望隐藏在画面的背后。

摄影有时给人会造成一种错觉,它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诞 生的,由于它的机械性,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利用机器的成像原理将我们已知和可见的事物通过平面再现而已,我认为,机械所带来的快捷性不应当成为创作意识的束缚,相机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力来实现创作思维,就像手握一支画笔一样。《道可道》是我用12◦胶片拍摄的作品,在我的眼里,我将所见到的带有符号性的景观予以柔焦与虚化,镜头中的对象因此变得抽象,说不清道不明,只剩下形与色,将人类最本质的权力欲望隐藏在画面的背后。

摄影有时给人会造成一种错觉,它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诞 生的,由于它的机械性,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利用机器的成像原理将我们已知和可见的事物通过平面再现而已,我认为,机械所带来的快捷性不应当成为创作意识的束缚,相机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力来实现创作思维,就像手握一支画笔一样。《道可道》是我用12◦胶片拍摄的作品,在我的眼里,我将所见到的带有符号性的景观予以柔焦与虚化,镜头中的对象因此变得抽象,说不清道不明,只剩下形与色,将人类最本质的权力欲望隐藏在画面的背后。

摄影有时给人会造成一种错觉,它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诞 生的,由于它的机械性,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利用机器的成像原理将我们已知和可见的事物通过平面再现而已,我认为,机械所带来的快捷性不应当成为创作意识的束缚,相机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力来实现创作思维,就像手握一支画笔一样。《道可道》是我用12◦胶片拍摄的作品,在我的眼里,我将所见到的带有符号性的景观予以柔焦与虚化,镜头中的对象因此变得抽象,说不清道不明,只剩下形与色,将人类最本质的权力欲望隐藏在画面的背后。

摄影有时给人会造成一种错觉,它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诞 生的,由于它的机械性,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利用机器的成像原理将我们已知和可见的事物通过平面再现而已,我认为,机械所带来的快捷性不应当成为创作意识的束缚,相机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力来实现创作思维,就像手握一支画笔一样。《道可道》是我用12◦胶片拍摄的作品,在我的眼里,我将所见到的带有符号性的景观予以柔焦与虚化,镜头中的对象因此变得抽象,说不清道不明,只剩下形与色,将人类最本质的权力欲望隐藏在画面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