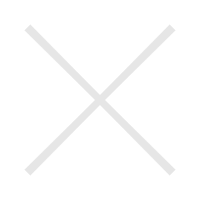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

经纬相交,独成画幅。生命的不被选择,是否正经历着扭转,线织的纵横穿插,意识的来回更替,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创造一种“戏剧性”冲突,其生命的厚重与交错的空间相叠加,是过去和当下在这里形成的一种矛盾体。且天地造世源生命,万物皆有灵,生命与传统相依缘而相伴,顺义个人记忆、怀旧与渴望想象的臆造,呈现出一幅理想主义的画面。